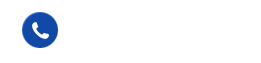陳寅恪一家在抗戰時期羈留香港,雖然時間不長,但是卻六次搬家,生活艱難可想而知。
1938年1月,長沙臨時大學奉命南遷云南昆明。陳寅恪攜家人登程,隨校流亡南行,途經香港。幾個月的路途顛簸,夫人唐篢心臟病突發,三女美延也高燒發熱,全家再也不能前行了。陳寅恪只得通過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夫婦租一住所暫留在香港。許地山當時擔任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教授、香港中英文化協會主席。陳寅恪的女兒們回憶當時見到許地山夫婦的情景:“許伯父身著長袍,鼻梁上架著一副黑邊大眼鏡,看起來雖然比父親年輕,卻已蓄了胡須。許伯母接近中年,高挑勻稱的身材,沒有多少客套話,乍見面時令人感到有點嚴肅,她主動提出把流求、小彭接到她家暫住,以便隔離,并減輕夫婦的勞累”。
許地山的夫人對香港地方很熟悉,她很快就代為租賃了一處距離她家不遠的房子,接著又跑前跑后幫著置備了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當時,許地山的家在羅便臣道125號,而為陳寅恪一家租賃的房子是羅便臣道104號,在一條街上,相距不遠。這是陳寅恪一家在香港的第一個家。
陳寅恪一家,在香港度過了逃難后的第一個春節。他們曾經商議,傭人王媽媽隨他們奔波半年,過舊歷年,總要讓她能吃幾塊肉。可是,因為經濟狀況實在惡劣,他們的這個善良的愿望也沒有實現。年后,陳寅恪必須趕往學校上課,夫人因勞頓心臟病發,體力不能支持,他們全家隨決定先由陳寅恪一人取道安南去云南蒙自。
也是在這年開春不久,他們一家第二次搬家到了九龍城附近的福佬村道11號三樓。為什么再次搬家,是因為當時許地山夫人幫助找的房子距離香港大學不遠,房租較貴,又加上是在半山腰,生活不便,所以才決定找一個既便宜一些,也不用爬坡的地方。他們新找的這個地方,比較偏僻,一室一廳的結構,又與另一個文化人、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沈乃正的家眷合租,兩家分攤之后,房租自然也便宜了很多。可是,搬來不久,陳寅恪的小女兒、剛滿周歲的美延染上了百日咳,因為沒有得到及時徹底的治療,又加上營養不足,嚴重影響了她的發育,以致后來到了入學年齡還不能去學校讀書。
當時,美延生病的時候,陳寅恪已經在云南。因為怕他擔心,夫人寫信從未提及過孩子生病的事。可是,所謂父女連心,陳寅恪似乎隱隱感覺到了孩子的健康出了問題。后來,三姐妹在他們的書中曾經這樣描述過他們的父親:“父親幾次對我們姐妹說過:曾在集市上偶然見到一位苗族婦女,背著個孩子,胖胖的眼睛挺大,很像美延,就盯著看;那婦女誤以為父親對小孩有什么歹心,帶著孩子趕快離去。”陳寅恪雖然乃一代大儒,但這件事讓我們看到他作為一個普通父親思念愛女的殷殷情懷。
1939年初,陳寅恪的妹妹陳新午帶著孩子來到香港,租賃了臨近跑馬地附近的樓房底層,為了能照顧她們,邀請陳寅恪的妻女一塊居住。她們就搬了過去,這也是陳寅恪一家在香港的第三處家。住房的后面因為就是一片墳地,常常有下葬祭奠的哭泣聲傳來,幾個孩子常常害怕。又因為那個地方很潮濕,孩子們常常生病。后來不久,陳夫人也生病住進了醫院。
到了6月份,陳夫人的病好了,但是,不適于再住在那個潮濕的地方,她們就又找了一個地方,九龍太子道,一幢樓房的頂層五樓。這是他們的第四個家。
但是不久,又因為陳夫人身體不好爬五樓很不方便,又第五次搬家到山林道24號三樓。
1939年陳寅恪被英國皇家學會授予研究員稱號,特聘他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這是300年來第一次由一個中國人任此教授,任期10月1日起。6月下旬,陳寅恪結束了西南聯大的課程由滇返港。對于去英國赴任,陳寅恪在1939年2月9日給傅斯年的信中說:“以經濟方面計算,似亦以全家同去為合算,且可免羈旅萬里,終日思家之苦。”
陳寅恪到達香港,在護照都已制作好的時候,因歐洲戰事,地中海無法通航,陳寅恪及家人只好暫居香港。陳寅恪9月5日致牛津大學函:“我原來打算在八月底乘船赴歐洲,并且萬事具備,由于局勢緊張和不明朗,我不得不等待數天。如今歐戰已經爆發,此時此刻,我已經不可能也不必要前往牛津……”
可是,無論如何,全家再次團圓了,孩子們很高興。
但是,由于這一段時間孩子和陳夫人接連生病,花費很大,陳寅恪一家的經濟狀況十分窘迫。他們決定再找一個更便宜一些的地段居住。
陳寅恪決定推遲一年赴英國就任,10月中旬啟程,依舊取海道乘船先去安南海防,然后坐火車到達昆明,返回西南聯大。
陳寅恪走后,還是許地山的夫人,請朋友與陳寅恪一家合租一套房子,既減輕房租負擔,也可以互相照顧。他們再次搬家到九龍太子道369號的三樓后座。這是陳寅恪一家在香港的第六次搬家,一直居住到香港淪陷全家逃到內地。
想象當年,一個中年女人,帶著三個女兒,在短短兩年之內,為生計所迫六次搬家,其顛沛流離的生活滋味不言而喻。
來自:廣州大眾搬家